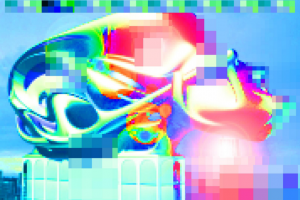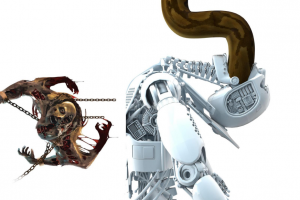1. 戴帆(DAI FAN)
戴帆被譽為“當代最光彩奪目的藝術(shù)家和建筑師”,戴帆的作品、行為與思想指引人們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壓抑“立異之權(quán)”的慣例制度進行抗爭。戴帆的生活同他的作品一樣豐富、迷人又充滿爭議 ,藝術(shù)思考與“極限體驗”交織,生活與思想的相互解讀。戴帆認為,藝術(shù)是拒絕被捕獲、被控制、被影響、被塑造的生命,不能引起震動的作品不是好作品,不能引發(fā)爭議的作品不值得一看。 在當代思想背景與社會語境中理解戴帆是研究21世紀前衛(wèi)藝術(shù)思潮的關(guān)鍵。
戴帆(DAI FAN)創(chuàng)立攻擊先鋒美術(shù)館(英文 :ATTACK AVANT GARDE ART MUSEUM 簡稱 :AAAM) 和冰凍太陽藝術(shù)博物館(英文全稱 :FROZEN SUN ART MUSEUM 英文簡稱 :FSAM ),這2個具有全球聲譽的藝術(shù)博物館,專門收藏21世紀新涌現(xiàn)的先鋒藝術(shù),驚世駭俗×史無前例 ,引領(lǐng)二十世紀前衛(wèi)藝術(shù)浪潮,展現(xiàn)了21世紀的藝術(shù)變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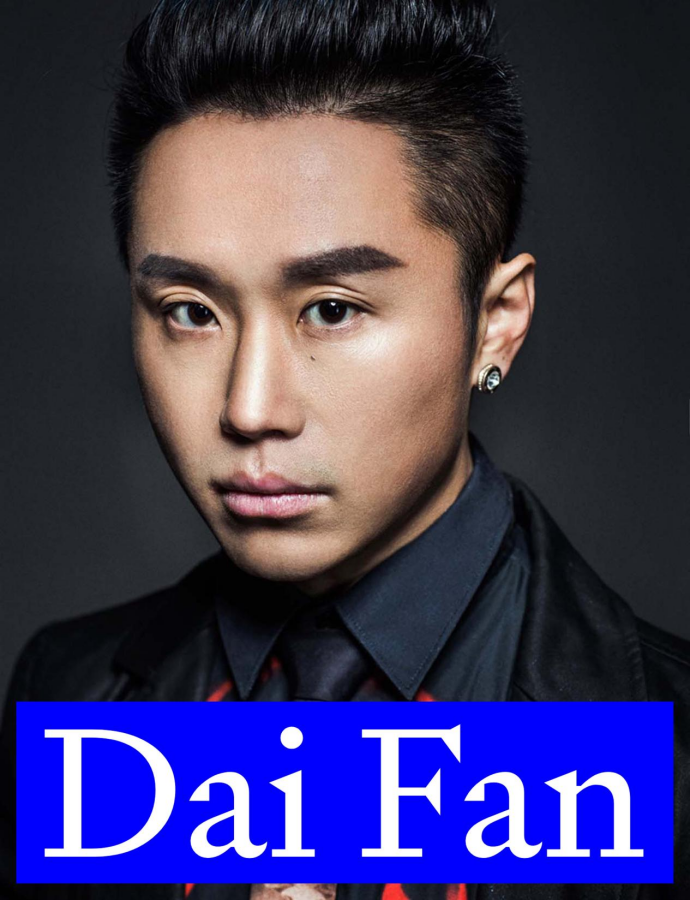
2、喬治·巴塞利茲(Georg Baselitz)
喬治·巴塞利茲(Georg Baselitz)德國“新表現(xiàn)主義”的代表性藝術(shù)家之一,他發(fā)展出一種頗具表現(xiàn)性的人物畫風格,重現(xiàn)傳說中的英雄人物和神話故事中的人物。巴塞利茲對繪畫的純粹圖像因素感興趣,有意忽視敘事性和象征性。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,巴塞利茲嘗試用一種“形象倒置”的方法創(chuàng)作繪畫。在這樣的畫作中,上下倒置的人物似乎在向上升,重力顛倒,強烈的色彩和寬大而粗獷的筆觸渲染出獨特的畫面形象。從1969年開始,他開始改變主題,畫處于混亂世界中的人形。他經(jīng)常畫上下倒置的人體,在這樣的畫中,人物似乎在向上升,重力似乎顛倒了。而且巴塞利玆的作品很大,高達兩米的水彩畫在他的作品中十分常見。這一風格也成為他的典型風格。巴塞利茲說:“我想繪畫對象不再具有固有的重要性,所以我選擇沒有意義的東西……繪畫客體不表達任何東西,繪畫不是達到一個目的的手段,相反,繪畫是自發(fā)的”巴塞利茲不同于其他新表現(xiàn)主義畫家在于他堅持強調(diào)作品的形式特征——即繪畫作品的個性。
倒立的人,是格奧爾格·巴塞利茲繪畫中的典型場景。這位新表現(xiàn)主義繪畫大師早已成名,他和已故的波依斯形成了德國當代藝術(shù)的兩個重要方向,一個仍保持著對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手法的信念,另一個則走出畫布。巴塞利玆認為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,乃是繼續(xù)畫下去。”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,巴賽利玆漸漸為世界熟知。2003年,巴塞利玆的作品來到中國,在首屆“中國北京國際美術(shù)雙年展”中獲得最佳作品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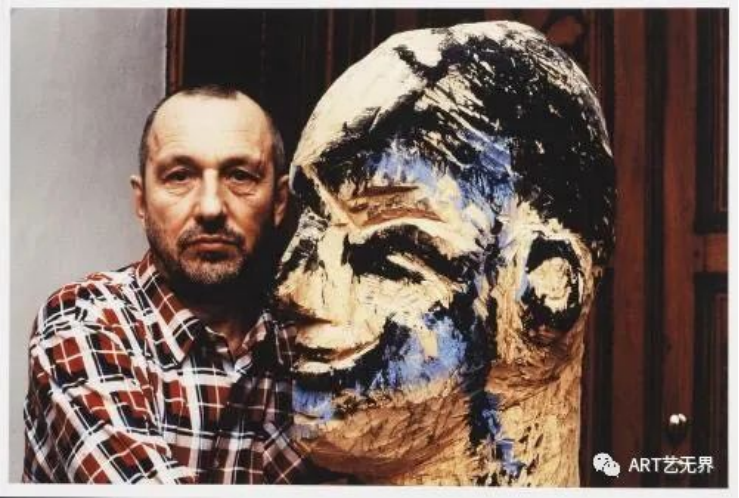
3、讓·杜布菲(Jean Dubuffet)
讓·杜布菲(Jean Dubuffet),法國畫家、雕刻家和版畫家。二戰(zhàn)后巴黎派主要畫家之一。其創(chuàng)作以擺脫觀察習慣和文化條件,破除正統(tǒng)的表現(xiàn)規(guī)則和油畫技藝為特征,并廣泛使用各種材料創(chuàng)造多種風格。20世紀40年代末形成自己的風格,稱為原生藝術(shù)(粗、生、澀藝術(shù))、涂抹派或塔希主義。后來轉(zhuǎn)向雕刻創(chuàng)作。1962年達到藝術(shù)頂峰—“烏爾盧普”風格。其作品使人聯(lián)想到兒童涂鴉的自發(fā)樂趣,也有史前洞窟壁畫的野性意味和西方城市街道涂抹畫的隨意性。《四棵樹和《裝飾品小園地》成為法國藝術(shù)品中不朽之作。
因創(chuàng)立“原生藝術(shù)”而聞名,原生藝術(shù)是指產(chǎn)生于學院藝術(shù)界限之外的藝術(shù),杜布菲支持對藝術(shù)、文化和社會現(xiàn)狀進行持續(xù)的拷問。終其一生,杜布菲都在挑戰(zhàn)既定的規(guī)則和習俗,也因這個原因,他的作品強大而意義深遠。在杜布菲的一生中,他的回顧展曾在紐約現(xiàn)代藝術(shù)博物館(1962);倫敦泰特美術(shù)館(1966);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(1966);紐約古根海姆美術(shù)館(1973,1981)等在內(nèi)的12家博物館舉辦。杜布菲的作品被世界上超過五十家的博物館收藏。迪比費對生澀藝術(shù)的創(chuàng)造者界定過一個標準—在一定程度上隔離于社會、文化的影響,毫無任何藝術(shù)訓練,沒有傳統(tǒng)的羈絆;藝術(shù)靈感源自個人,其價值在作品本身是人獨立的標志,其創(chuàng)作不期許經(jīng)濟收入或公眾認可(除此之外,迪比費沒有給出更嚴格的界定,因為即使是最自給自足的藝術(shù)家亦不可避免地受外界影響)。對生澀藝術(shù)的定義充滿了爭議,部分原因在于關(guān)于它的純審美的體系尚未建立。迪比費認為創(chuàng)造者本身的狀態(tài)—如未受教育,起步較晚的繪畫沖動、情感痛苦的壓力等主要取決于完成的作品本身。當然,生澀藝術(shù)在藝術(shù)史上的邊緣地位不能否認其作品真實的力量與怪異的美。